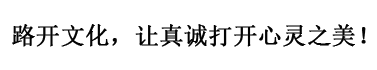□文/曾桂

2015年1月下旬的一个上午,我们夫妻去参加堂弟第二个女儿的婚宴。
妻子穿着黑色上衣红色裤子,这种年纪穿红色裤子真是少见。我调侃了她几句,她心态倒是不错,说现在不穿,以后就不好穿了,别人六十多还穿一身红呢。
驱车几十公里到达洛口圆布村,再进六七公里到达一个路口,将车放在路边,徒步走了一段两百多米崎岖坡道,这坡道依旧是砂石路。
见到堂弟,打过招呼,我说了些祝贺的客气话,送上一个红包。看到他忙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的,我便主动退到外面来。
来了很多客人。小孩子追追打打嘻嘻哈哈;女人扎堆聊着家长里短鸡毛蒜皮,不时地爆发出阵阵大笑;青壮年男性抽烟打扑克,吆五喝六;老头老太太则是鸡同鸭讲。
有一些亲戚,我跟他们平常少有来往,彼此都觉得陌生。坐在一起只是打打哈哈,为避免尴尬,我拿上相机出去到处乱拍。

村子小,只有十几户人家,房子都比较低矮且旧,堂弟的房子在村里是最气派的。那些条件好的都搬出去了。
四下一片荒芜,没有什么好风景,不到二十分钟我便回来了。
侄子过来跟我打招呼,他在汕头做生意,一年下来有二十万左右的收入,很不错。今年二十九,还没有谈女朋友。在乡村这年纪已经很大了,父母很着急,可是束手无策。
今天出嫁的是堂弟的二女儿,已经有了一个小孩,据说肚子里又有了一个。现在奉子成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极为羞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。如今未婚同居养男育女已是常态,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再过一个三十年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?我缺乏这种想象力。
堂弟以我能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为荣,他把我看成是他的显亲。

堂弟把几个女儿叫到我身边来让我认识:老大已经结婚多年,有了两个小孩,大女婿是外省人;老二今天出嫁,嫁给一个开理发店的洛口古夏人,新郎戴着耳钉,这让我看了有些不适;老三是儿子;老四乖巧伶俐,三姐妹中她最漂亮,已谈了男友,四川人。
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婚姻半径很大,当年能出县就觉得很远很远,跨地区乃至跨省是不可思议的,而这都得益于改革开放。
堂弟拉着我跟几个老人家打招呼,得知我是当年的瘦牯子,老人们很是惊讶,恍如隔世。回忆往事,一副感概万千的样子。当年我父亲住在距离这里几十里的小村,那是一个更为偏僻更为穷苦的地方。
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我父亲,他们对我小时候的遭遇多有了解多有同情,现在我的变化是他们没有想到的,所以很是惊讶。
我一直有个想法,到我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。

乡村的午饭一般都比较迟,婚宴就更迟,拖到将近一点才开席。
我坐的这一桌有两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家,上席有两个位子,他们礼让着左右,推了半天。老人家都是比较讲究的,在这一桌我没有坐上席的资格。邻桌的上席坐的是两个三十几岁的女人,显然他们并不讲究。现在讲究这些规矩的人少了,我觉得是好事,生活节奏快,不需要繁文缛节。
我要开车所以就不喝酒。另外几个包括那两个老人家都喝酒,红酒。席间他们频频举碗,乡村酒席不用杯子都是用碗装酒。菜很不错,尤其是那份芋子蒸排骨,香极了,芋子烂透入味。乡村办酒席很在意别人的评价,只要有条件都会在材料上不惜工本。
大约一个小时就散席了。我坐了几分钟告辞,堂弟家来了这么多客人,他很忙,我不能增加他的负担,再说我想回去午休,否则晚上就没有精神。
我跟几个老少亲戚握手,叮嘱小侄女跟他男朋友以后来我家做客,然后告辞。
摄影 小夫(路开文化)
曾桂,赣州宁都人,某教育机构负责人。

2015年1月下旬的一个上午,我们夫妻去参加堂弟第二个女儿的婚宴。
妻子穿着黑色上衣红色裤子,这种年纪穿红色裤子真是少见。我调侃了她几句,她心态倒是不错,说现在不穿,以后就不好穿了,别人六十多还穿一身红呢。
驱车几十公里到达洛口圆布村,再进六七公里到达一个路口,将车放在路边,徒步走了一段两百多米崎岖坡道,这坡道依旧是砂石路。
见到堂弟,打过招呼,我说了些祝贺的客气话,送上一个红包。看到他忙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的,我便主动退到外面来。
来了很多客人。小孩子追追打打嘻嘻哈哈;女人扎堆聊着家长里短鸡毛蒜皮,不时地爆发出阵阵大笑;青壮年男性抽烟打扑克,吆五喝六;老头老太太则是鸡同鸭讲。
有一些亲戚,我跟他们平常少有来往,彼此都觉得陌生。坐在一起只是打打哈哈,为避免尴尬,我拿上相机出去到处乱拍。

村子小,只有十几户人家,房子都比较低矮且旧,堂弟的房子在村里是最气派的。那些条件好的都搬出去了。
四下一片荒芜,没有什么好风景,不到二十分钟我便回来了。
侄子过来跟我打招呼,他在汕头做生意,一年下来有二十万左右的收入,很不错。今年二十九,还没有谈女朋友。在乡村这年纪已经很大了,父母很着急,可是束手无策。
今天出嫁的是堂弟的二女儿,已经有了一个小孩,据说肚子里又有了一个。现在奉子成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极为羞耻的也是不可想象的。如今未婚同居养男育女已是常态,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再过一个三十年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?我缺乏这种想象力。
堂弟以我能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为荣,他把我看成是他的显亲。

堂弟把几个女儿叫到我身边来让我认识:老大已经结婚多年,有了两个小孩,大女婿是外省人;老二今天出嫁,嫁给一个开理发店的洛口古夏人,新郎戴着耳钉,这让我看了有些不适;老三是儿子;老四乖巧伶俐,三姐妹中她最漂亮,已谈了男友,四川人。
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婚姻半径很大,当年能出县就觉得很远很远,跨地区乃至跨省是不可思议的,而这都得益于改革开放。
堂弟拉着我跟几个老人家打招呼,得知我是当年的瘦牯子,老人们很是惊讶,恍如隔世。回忆往事,一副感概万千的样子。当年我父亲住在距离这里几十里的小村,那是一个更为偏僻更为穷苦的地方。
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我父亲,他们对我小时候的遭遇多有了解多有同情,现在我的变化是他们没有想到的,所以很是惊讶。
我一直有个想法,到我出生的地方去看一看。

乡村的午饭一般都比较迟,婚宴就更迟,拖到将近一点才开席。
我坐的这一桌有两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家,上席有两个位子,他们礼让着左右,推了半天。老人家都是比较讲究的,在这一桌我没有坐上席的资格。邻桌的上席坐的是两个三十几岁的女人,显然他们并不讲究。现在讲究这些规矩的人少了,我觉得是好事,生活节奏快,不需要繁文缛节。
我要开车所以就不喝酒。另外几个包括那两个老人家都喝酒,红酒。席间他们频频举碗,乡村酒席不用杯子都是用碗装酒。菜很不错,尤其是那份芋子蒸排骨,香极了,芋子烂透入味。乡村办酒席很在意别人的评价,只要有条件都会在材料上不惜工本。
大约一个小时就散席了。我坐了几分钟告辞,堂弟家来了这么多客人,他很忙,我不能增加他的负担,再说我想回去午休,否则晚上就没有精神。
我跟几个老少亲戚握手,叮嘱小侄女跟他男朋友以后来我家做客,然后告辞。
摄影 小夫(路开文化)
▼


曾桂,赣州宁都人,某教育机构负责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