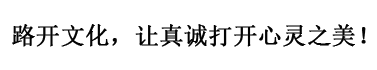□文/谢平

1
新安车站其实是没有车站的,从来也没有过。只是它为206国道枢纽之地,北往头陂镇再通宁都县,南去赤水镇再通石城县,附近老表去往两处赶墟就会在这里搭班车或者便车,于是就把它称为车站了。
车站东面建了两栋砖墙房,为供销社。坡上的那栋平房是办公室、五金店、收购站;坡底的那栋为二层楼,第一层是百货店、饮食店、售肉部,第二层的边上是住宿部,其余的是职工宿舍。
那时,我妈在百货店当营业员,时常有外地的司机来这歇脚,他们开着大货车,在路口刹了车,后面卷起的尘土扑面而来。跳下车的外地司机一个个篷头垢面,皮肤黝黑,走进店里,打几两散装红薯酒,买一斤水饼,倚着柜台吃,吃完聊一会天,等酒气散去就上路了。我妈有一段时间叫我“江苏佬”,缘于我晒黑的皮肤与那些司机没有两样。
早上,饮食部的李师傅在门口支一口大锅煎油条,发酵好的面切成两指宽,两块叠好,再用筷子在中间压出一道印,拎起,一半浸入热油里再拧一下放倒,油条马上泡浮起来,呈金黄色,香气四溢(虽然我每天都能看到这种情景,但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得起)。
黄师傅的老婆,一个高大肥胖女人,负责售卖。她用她粗壮的手臂夹起油条放在盘子上,舀一勺豆浆倒进碗里,顾客一手托盘,一手端碗,嘴巴上还叼着一根油条,往屋里去找坐。豆浆是前一天晚上黄师傅夫妻磨出来的,厨房里个有一个大石磨,专门用来磨豆腐豆浆,石磨边的手把套上二根长杆供两人推送。黄嫂肥胖的身躯运动了一阵就大汗淋漓,湿透了衣服,他们夫妻干脆趁只有两人在场,脱了衣服,赤膊上阵,黄嫂硕大的双乳随着二根长杆一拉一送晃荡着,搅动得空气呼呼作响。

2
进入夏季,马路两边乌桕树、苦楝树上的知了开始鸣叫,我们会用蛛丝沾些水不停在手上揉,揉成团有了粘性,就把它粘在几米长的竹子顶端。到了树底下,知了觉察有人就会停止鸣叫,所以竹子要足够长,在知了感觉安全之外的长度才能够轻松粘住它。知了可以吃,据说头部有块肉跟猪肉一样,煨了吃特别香,但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尝试,像炸蜂蛹、蚕蛹、蚂蚱之类的东西,我有一种强烈的拒绝心理。
在这个季节,乌桕树开始结果,青色的算盘子大小的乌桕果里面藏着四粒白色的籽,那是做肥皂的原料,一斤的价钱能抵得上半斤肉价。我们把结满果的树枝拗下来,放在太阳下曝晒,几天后果壳裂开,露出洁白的乌桕籽。
我在车站居住的三年时间里,是我这辈子体力活做得最多的时间段。不用家长驱使,我完全融入周围同龄段孩子的劳动生活中去。上山采摘金樱子、黄桅子,它们的价格在收购部的“收购栏”标得清清楚楚;下河摸石头、挑沙子卖给养路队,哪里拆房子,就去打工,削拆下来砖头周边的泥浆……此外,砍柴、挖猪菜、盘泥鳅、拣田螺、拾稻穗等等,充斥在读书之外的时间里。
收割完晚稻,就进入农闲季节,宁都的菜贩子最先入驻在住宿部。他们用鸡公车推来一麻袋一麻袋的“葛薯”(白薯),以车站为中心,售卖到各个村队。宁都产的葛薯爽脆清甜,既可当水果吃又能做菜,还能和肉做馅,做包子肉丸。
这些“宁都佬”说的是客家话,大致能听懂。他们说“4”这个数,忌讳与“死”同音,就说“红数噶”。暑期我们兄弟姐妹都回到爸妈身边,房间不够,我就借住了住宿部的一个床位。他们喜欢裸睡,有一则笑话就与此有关。说是某晚,一“宁都佬”尿急,尿完,工具没滴沥干净,跨过睡在床上老婆的头,一滴尿液准确滴在老婆的嘴里,老婆感觉嘴唇上有咸味,迷迷糊糊骂起来:“死了噶,半夜三更还去偷腌菜吃哒?”老公就说“我没。”“还没?滴在我嘴里还咸咸的。”

3
接着,卖麦芽糖的“抚州佬”也住进来,我们叫这种人是“叮叮壳”,他们走家串户,敲着切麦牙糖的铁板“叮壳,叮壳,叮叮壳”。
“抚州佬”是一个老头,走路慢悠悠,还有些气喘。他不裸睡,穿一条宽大的短裤,翻晒完收来的鸭毛鹅毛,分拣好旧塑料、牙膏皮、薄膜片就去洗澡。他提半桶冷水,用长长的汗巾按部就班地从头到脚、从前到后搓洗。他胸前松弛的肉无精打采耷拉下来,一层又一层。洗完,穿上汗褂、宽头裤,趿上拖鞋,上楼,在房间里对着镜子,把头上稀疏的头发往后梳,脸上红白相间,显得焕然一新。
晚上,他借小吃部的锅熬麦芽糖,麦牙糖呈暗红色,冒着热气,他吭哧一声,把一整块的麦牙糖甩在准备好的横杆上。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拉扯,直到暗红的颜色变成白色。
开始的时候麦牙糖有些滚烫,他就在冷水里浸一下接着拉,来不及就干脆拍拍手,往手心里吐唾沫。这个不卫生的举动被我发现了,我就再也不吃他的麦牙糖了,还提醒我的小伙伴:“抚州佬的麦牙糖好吃吗?”“怎么了?”“是不是多有一股口水味?”伙伴们很惊讶,从此也不吃了。“抚州佬”听到这个消息,气得直骂:“哪个短命鬼造个谣,害得我的糖卖不得!”

4
后来,“抚州佬”搬到商店后面农户家居住,房东叫“侯姑”,也是我家的房东,我家租了她家一间厨房。“侯姑”是寡妇,嘴角老是抽搐,就像东北二人转那个“尼古拉赵四”。有人可能会认为“侯姑”与“抚州佬”有什么可写的故事,其实什么都没有,“抚州佬”就是贪图房租便宜,有时候还能蹭饭吃。陆续住进住宿部的还有于都来的弹棉花师傅,以及捉“水鸡”(甲鱼)的“打鱼佬”。
弹棉花的师傅是商店请来的,于都梓山人(于都梓山出去打工的,基本都是带着弹棉花的手艺)。他们在商店后面的肥料仓库里要忙上一个月,弹好的棉花就被捆好码在货架顶上,等待顾客选购。这个月里,每天都能听到屋后传来的声音,“嘣嘣嘣——铿”。
弹棉师傅后背绑有护带,一张巨大的弓从他的头顶吊起,他左手握弓背,右手拿木棰,木棰有节奏敲击牛筋线,声音就是敲击这根牛筋发出来的。随着声音,沾在牛筋线上的棉絮被震颤得散开,雪花般落下,牛筋线又沾上它们,震颤得更加细碎地飘落下来。弹棉师傅的头发上身上落满了棉絮,一个壮年瞬即变成了皓首老人。
“打鱼佬”带的工具就是一根长竹杆,一端套有铁皮尖刺,这是用来刺探水底情况,碰到硬物可以顶开。因为塘主都不会放“水鸡”苗,所以任由“打鱼佬”到池塘折腾,“打鱼佬”先站在岸上观察水情,确定可能水下有“水鸡”才下水。
“打鱼佬”蹚到池塘中央,四周观察一阵,跃起,两只手成弯弓状猛力砸向水面,“嘣—嘣”声音沉闷而有力。不一会儿,水面上的某处就会升起一串串的水泡,这大概率是“水鸡”吐出的泡,大约它是受不了惊忧或是缺氧了,吐着气冒出水面。天然“水鸡”是滋补佳品,炖汤鲜美无比,现在却难以吃到,市场上碰到也难辨真假,而且价格奇贵……
一天,我打电话问新安老六仔,商店还在吗?他说,早倒塌了,野草野树生长茂盛。并发给我照片作证。
供图 谢平(路开文化)
谢平,江西广昌人,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,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,现居广昌。教育系统工作,散文作品见《厦门日报》等报刊,赣州路开文化文友。

1
新安车站其实是没有车站的,从来也没有过。只是它为206国道枢纽之地,北往头陂镇再通宁都县,南去赤水镇再通石城县,附近老表去往两处赶墟就会在这里搭班车或者便车,于是就把它称为车站了。
车站东面建了两栋砖墙房,为供销社。坡上的那栋平房是办公室、五金店、收购站;坡底的那栋为二层楼,第一层是百货店、饮食店、售肉部,第二层的边上是住宿部,其余的是职工宿舍。
那时,我妈在百货店当营业员,时常有外地的司机来这歇脚,他们开着大货车,在路口刹了车,后面卷起的尘土扑面而来。跳下车的外地司机一个个篷头垢面,皮肤黝黑,走进店里,打几两散装红薯酒,买一斤水饼,倚着柜台吃,吃完聊一会天,等酒气散去就上路了。我妈有一段时间叫我“江苏佬”,缘于我晒黑的皮肤与那些司机没有两样。
早上,饮食部的李师傅在门口支一口大锅煎油条,发酵好的面切成两指宽,两块叠好,再用筷子在中间压出一道印,拎起,一半浸入热油里再拧一下放倒,油条马上泡浮起来,呈金黄色,香气四溢(虽然我每天都能看到这种情景,但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得起)。
黄师傅的老婆,一个高大肥胖女人,负责售卖。她用她粗壮的手臂夹起油条放在盘子上,舀一勺豆浆倒进碗里,顾客一手托盘,一手端碗,嘴巴上还叼着一根油条,往屋里去找坐。豆浆是前一天晚上黄师傅夫妻磨出来的,厨房里个有一个大石磨,专门用来磨豆腐豆浆,石磨边的手把套上二根长杆供两人推送。黄嫂肥胖的身躯运动了一阵就大汗淋漓,湿透了衣服,他们夫妻干脆趁只有两人在场,脱了衣服,赤膊上阵,黄嫂硕大的双乳随着二根长杆一拉一送晃荡着,搅动得空气呼呼作响。

2
进入夏季,马路两边乌桕树、苦楝树上的知了开始鸣叫,我们会用蛛丝沾些水不停在手上揉,揉成团有了粘性,就把它粘在几米长的竹子顶端。到了树底下,知了觉察有人就会停止鸣叫,所以竹子要足够长,在知了感觉安全之外的长度才能够轻松粘住它。知了可以吃,据说头部有块肉跟猪肉一样,煨了吃特别香,但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尝试,像炸蜂蛹、蚕蛹、蚂蚱之类的东西,我有一种强烈的拒绝心理。
在这个季节,乌桕树开始结果,青色的算盘子大小的乌桕果里面藏着四粒白色的籽,那是做肥皂的原料,一斤的价钱能抵得上半斤肉价。我们把结满果的树枝拗下来,放在太阳下曝晒,几天后果壳裂开,露出洁白的乌桕籽。
我在车站居住的三年时间里,是我这辈子体力活做得最多的时间段。不用家长驱使,我完全融入周围同龄段孩子的劳动生活中去。上山采摘金樱子、黄桅子,它们的价格在收购部的“收购栏”标得清清楚楚;下河摸石头、挑沙子卖给养路队,哪里拆房子,就去打工,削拆下来砖头周边的泥浆……此外,砍柴、挖猪菜、盘泥鳅、拣田螺、拾稻穗等等,充斥在读书之外的时间里。
收割完晚稻,就进入农闲季节,宁都的菜贩子最先入驻在住宿部。他们用鸡公车推来一麻袋一麻袋的“葛薯”(白薯),以车站为中心,售卖到各个村队。宁都产的葛薯爽脆清甜,既可当水果吃又能做菜,还能和肉做馅,做包子肉丸。
这些“宁都佬”说的是客家话,大致能听懂。他们说“4”这个数,忌讳与“死”同音,就说“红数噶”。暑期我们兄弟姐妹都回到爸妈身边,房间不够,我就借住了住宿部的一个床位。他们喜欢裸睡,有一则笑话就与此有关。说是某晚,一“宁都佬”尿急,尿完,工具没滴沥干净,跨过睡在床上老婆的头,一滴尿液准确滴在老婆的嘴里,老婆感觉嘴唇上有咸味,迷迷糊糊骂起来:“死了噶,半夜三更还去偷腌菜吃哒?”老公就说“我没。”“还没?滴在我嘴里还咸咸的。”

3
接着,卖麦芽糖的“抚州佬”也住进来,我们叫这种人是“叮叮壳”,他们走家串户,敲着切麦牙糖的铁板“叮壳,叮壳,叮叮壳”。
“抚州佬”是一个老头,走路慢悠悠,还有些气喘。他不裸睡,穿一条宽大的短裤,翻晒完收来的鸭毛鹅毛,分拣好旧塑料、牙膏皮、薄膜片就去洗澡。他提半桶冷水,用长长的汗巾按部就班地从头到脚、从前到后搓洗。他胸前松弛的肉无精打采耷拉下来,一层又一层。洗完,穿上汗褂、宽头裤,趿上拖鞋,上楼,在房间里对着镜子,把头上稀疏的头发往后梳,脸上红白相间,显得焕然一新。
晚上,他借小吃部的锅熬麦芽糖,麦牙糖呈暗红色,冒着热气,他吭哧一声,把一整块的麦牙糖甩在准备好的横杆上。接下来就是不断地拉扯,直到暗红的颜色变成白色。
开始的时候麦牙糖有些滚烫,他就在冷水里浸一下接着拉,来不及就干脆拍拍手,往手心里吐唾沫。这个不卫生的举动被我发现了,我就再也不吃他的麦牙糖了,还提醒我的小伙伴:“抚州佬的麦牙糖好吃吗?”“怎么了?”“是不是多有一股口水味?”伙伴们很惊讶,从此也不吃了。“抚州佬”听到这个消息,气得直骂:“哪个短命鬼造个谣,害得我的糖卖不得!”

4
后来,“抚州佬”搬到商店后面农户家居住,房东叫“侯姑”,也是我家的房东,我家租了她家一间厨房。“侯姑”是寡妇,嘴角老是抽搐,就像东北二人转那个“尼古拉赵四”。有人可能会认为“侯姑”与“抚州佬”有什么可写的故事,其实什么都没有,“抚州佬”就是贪图房租便宜,有时候还能蹭饭吃。陆续住进住宿部的还有于都来的弹棉花师傅,以及捉“水鸡”(甲鱼)的“打鱼佬”。
弹棉花的师傅是商店请来的,于都梓山人(于都梓山出去打工的,基本都是带着弹棉花的手艺)。他们在商店后面的肥料仓库里要忙上一个月,弹好的棉花就被捆好码在货架顶上,等待顾客选购。这个月里,每天都能听到屋后传来的声音,“嘣嘣嘣——铿”。
弹棉师傅后背绑有护带,一张巨大的弓从他的头顶吊起,他左手握弓背,右手拿木棰,木棰有节奏敲击牛筋线,声音就是敲击这根牛筋发出来的。随着声音,沾在牛筋线上的棉絮被震颤得散开,雪花般落下,牛筋线又沾上它们,震颤得更加细碎地飘落下来。弹棉师傅的头发上身上落满了棉絮,一个壮年瞬即变成了皓首老人。
“打鱼佬”带的工具就是一根长竹杆,一端套有铁皮尖刺,这是用来刺探水底情况,碰到硬物可以顶开。因为塘主都不会放“水鸡”苗,所以任由“打鱼佬”到池塘折腾,“打鱼佬”先站在岸上观察水情,确定可能水下有“水鸡”才下水。
“打鱼佬”蹚到池塘中央,四周观察一阵,跃起,两只手成弯弓状猛力砸向水面,“嘣—嘣”声音沉闷而有力。不一会儿,水面上的某处就会升起一串串的水泡,这大概率是“水鸡”吐出的泡,大约它是受不了惊忧或是缺氧了,吐着气冒出水面。天然“水鸡”是滋补佳品,炖汤鲜美无比,现在却难以吃到,市场上碰到也难辨真假,而且价格奇贵……
一天,我打电话问新安老六仔,商店还在吗?他说,早倒塌了,野草野树生长茂盛。并发给我照片作证。
供图 谢平(路开文化)
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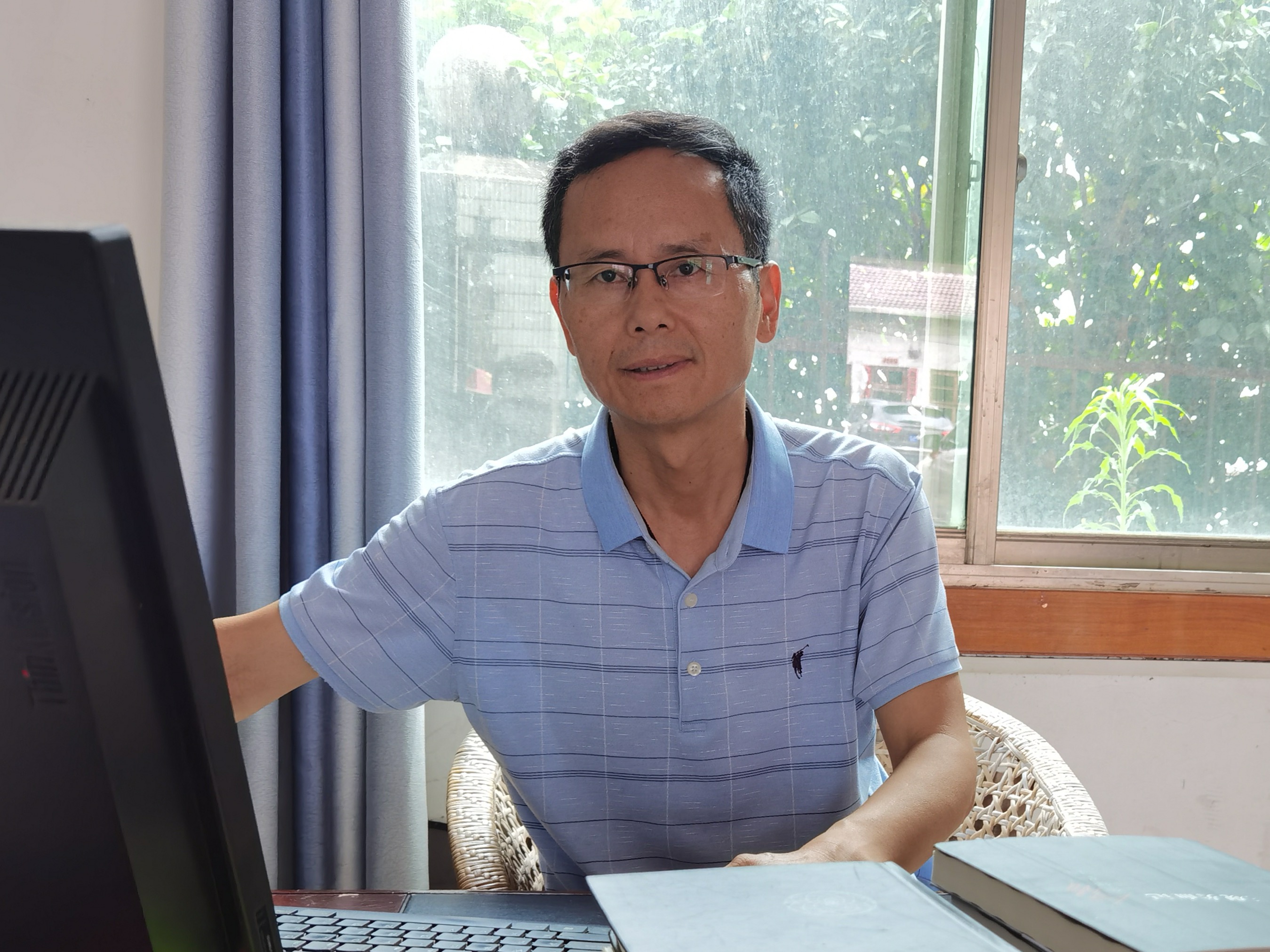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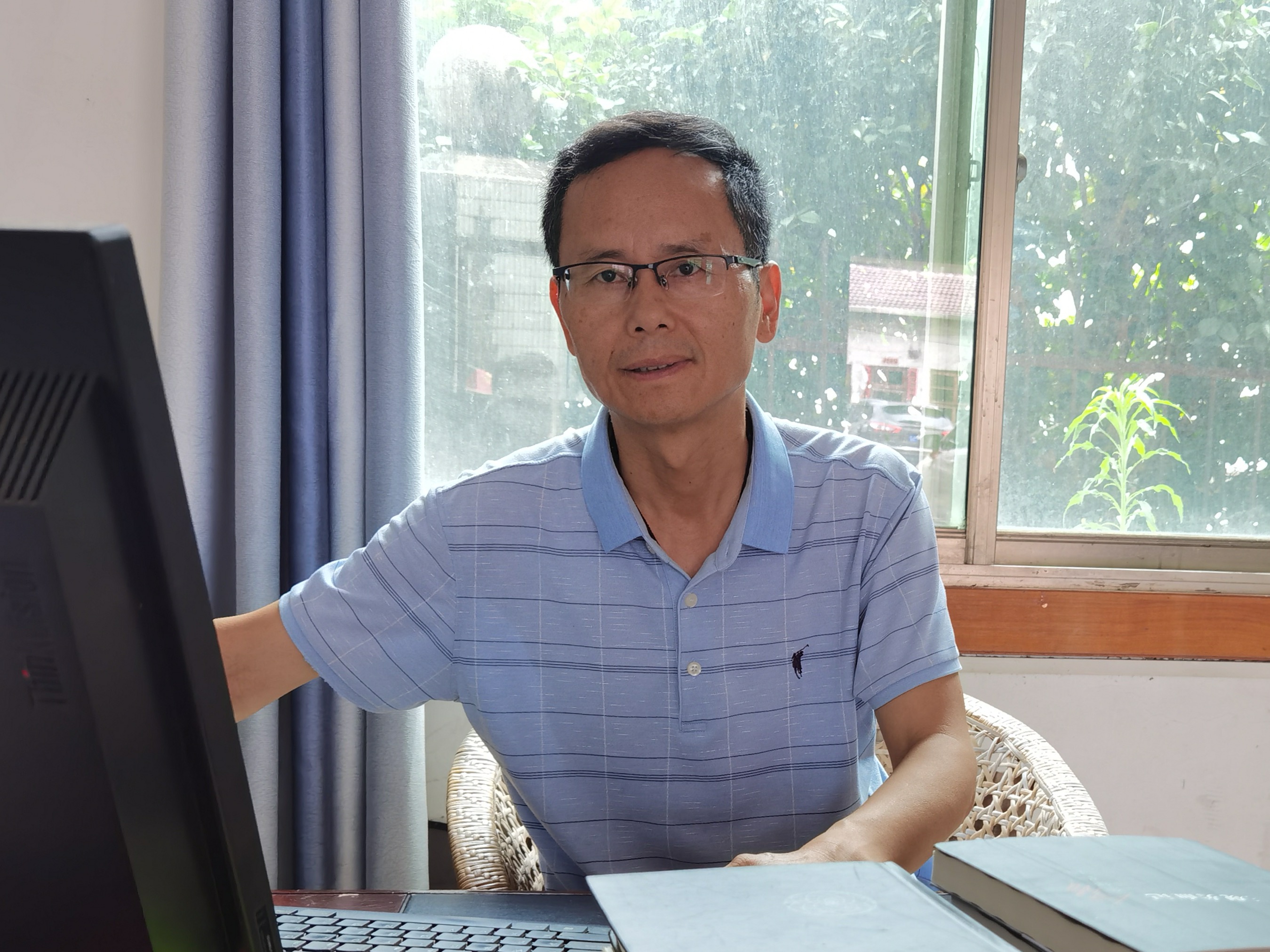
谢平,江西广昌人,赣南师范大学1980级中文就读,曾为天津某物流公司总经理,现居广昌。教育系统工作,散文作品见《厦门日报》等报刊,赣州路开文化文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