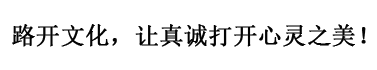□文/沈丽华

下午,母亲打来电话:“小琴啊,你爸生病了,上吐下泻,你们快过来看看吧!”
接听完电话,琴转身抓起手提包,心急火燎地就往弟弟家跑去。
望着躺在床上、嘴里哼哼唧唧的老父亲,琴说:“老爸,您今天吃什么东西了,是不是西瓜吃多了?”
琴知道的,父亲爱吃西瓜。
最近气候炎热,本地西瓜正大量上市。华溪镇的西瓜可好吃了,又沙又甜很解渴,满街都是卖瓜的摊点。
父亲不好意思地点点头,有些难为情地说:“是吃了点西瓜,不多啊,主要是还吃了几个酸李子。”那表情,活脱脱一个老小孩。
琴说:“没事,没事。起床,上医院,看医生!”
来到医院,测体温、化验大小便后,美女医生说:“老人家,是急性肠胃炎,要打几天吊针了,住院吧。”
父亲听说要住院治疗,头都大了,他最怕打针。

琴做主说:“老爸,听医生的话,您年龄已高,不能大意,即来之则安之。”
进得病房,同房的病床上已经住了一位病友,也在打吊针。琴看了一眼床上的挂牌:76岁,心脑血管病,胃肠不适,睡眠障碍。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有一位男子,正低头看手机。
经过两天的精心治疗,父亲的病情明显好转,每天送去的可口饭菜都一扫而光, 让对床的病友很是羡慕。
病友说:“大哥,你好福气啊,能吃能睡,昨天晚上我听了你一夜的鼾声。”
父亲说:“啊呀,大兄弟,対不起了,影响你睡觉了。为什么不叫醒我呢?”
病友说:“没事,没事,叫醒你,我已睡不着啊!”
父亲说:“兄弟,你的病好些没有?”
病友答:“我的病啊,一时半会很难好利索的,我自己知道的。我啊,一半是身体病,一半是心病,心病还需心药治啊。”
琴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,能够听到两位老人的对话。

病友说:“老哥,还是你养个姑娘好啊,天天陪你打吊针,嘘寒问暖。”
父亲说:“都好,都好。你儿子也经常来看你哦。兄弟,你有什么心病,能告诉我吗?”
父亲这一问,病友便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题。
老哥啊,我有两个儿子,一个开货车跑运输,一个在家盘田种地,都已成家立业。两个儿子分家后,我则和老伴共同生活。
半年前,两个儿子商量,决定帮我们养老,按照农村的风俗,大儿子养爹,小儿子养娘。
听到儿子们的安排后,我第一是高兴,孩子们没有忘记养育之恩,能反哺父母了。第二是担忧,我们年事已高,不论做什么事也力不从心了,只会给孩子们增加负担。还有,我们两个老人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与年轻人会有冲突,能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吗?
一天晩上,我再次与老伴商量,看看该作何选择。
老伴默默地从床头柜抽屉里摸出来一本银行存折。唉,忙了一辈子,累了一辈子,熬了一辈子,苦了一辈子,存折里的金额实在羞于见人,远远不足以承载今后生老病死的支出。
夫妻俩四目相对,一脸的无奈和心酸。

老伴说:“不用商量了,随了孩子们的心愿吧,养儿不就是为了防老吗?”
我只有应和着说,好吧,听您的,谁让我们的“腰窝油”不肥厚(歇后语,云南人形容钱少)呢!
不日,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老夫妻,收拾起简单的行李,一步一回头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,相互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,各自搬进了儿子们安排好的楼房里,开始了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。
我是做爹的,住大儿子家。住进儿子家才半个月,就感到浑身不舒坦。
儿子早出晚归跑运输,儿媳对我也很客气,客气到有点生疏冷漠。
儿媳喜欢打麻将,早饭后手机里不时传来"三缺一"的催促声。
每个白天,孙子去上学,我除了看看电视或到村口大榕树下找老伙伴拉拉家常外,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。
做晚饭的时间到了,儿媳迟迟未归。我呢,总不能袖手旁观地等人伺候吧,只好淘米择菜,洋相百出地学习做饭炒菜。
饭桌上,儿媳的脸上有时阴雨绵绵,有时嘴里嘟嘟哝哝,明显表示我做的饭菜不对味口,我心生愧疚,忐忑不安。

想多了心情就不爽,吃不下饭。
夜深人静的时候,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,我心里寡淡寡淡的,翻来覆去睡不着觉,十二分地想念我那在同一口锅里吃了几十年饭菜的老伴。
从前,与老伴虽然住在条件简陋的老宅里,但每天形影不离、相依相伴、彼此抚慰,有病互相精心地服伺,没病耐心地陪伴,吃着粗茶淡饭,也觉得很适合胃口,很满足。而现在,想想心里就堵得慌。
人老啰,不中用了!
唉,紧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,
琴听见父亲安慰道:“兄弟,想开一点吧,我们这些人以前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罪还少吗?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告诉自己的儿子,不能老憋在心里。
我有时也想,人老了,都会遇到很多问题,能及时解决当然是最好的了,接受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态度,最糟糕的就是既没有能力解决问题,又不愿意接受现状,每天抱怨,闷闷不乐,把自己的生活活成死局。有了这种心病,就像你自己所说的,那就真的无药可治了!”
病房内没有声音了,两位老人都陷入了沉默。
琴坐在病房外,两位老人的对话清晰地传进她的耳朵里,她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,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摄影 小夫(路开文化)
沈丽华,云南玉溪人,退休。

下午,母亲打来电话:“小琴啊,你爸生病了,上吐下泻,你们快过来看看吧!”
接听完电话,琴转身抓起手提包,心急火燎地就往弟弟家跑去。
望着躺在床上、嘴里哼哼唧唧的老父亲,琴说:“老爸,您今天吃什么东西了,是不是西瓜吃多了?”
琴知道的,父亲爱吃西瓜。
最近气候炎热,本地西瓜正大量上市。华溪镇的西瓜可好吃了,又沙又甜很解渴,满街都是卖瓜的摊点。
父亲不好意思地点点头,有些难为情地说:“是吃了点西瓜,不多啊,主要是还吃了几个酸李子。”那表情,活脱脱一个老小孩。
琴说:“没事,没事。起床,上医院,看医生!”
来到医院,测体温、化验大小便后,美女医生说:“老人家,是急性肠胃炎,要打几天吊针了,住院吧。”
父亲听说要住院治疗,头都大了,他最怕打针。

琴做主说:“老爸,听医生的话,您年龄已高,不能大意,即来之则安之。”
进得病房,同房的病床上已经住了一位病友,也在打吊针。琴看了一眼床上的挂牌:76岁,心脑血管病,胃肠不适,睡眠障碍。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坐有一位男子,正低头看手机。
经过两天的精心治疗,父亲的病情明显好转,每天送去的可口饭菜都一扫而光, 让对床的病友很是羡慕。
病友说:“大哥,你好福气啊,能吃能睡,昨天晚上我听了你一夜的鼾声。”
父亲说:“啊呀,大兄弟,対不起了,影响你睡觉了。为什么不叫醒我呢?”
病友说:“没事,没事,叫醒你,我已睡不着啊!”
父亲说:“兄弟,你的病好些没有?”
病友答:“我的病啊,一时半会很难好利索的,我自己知道的。我啊,一半是身体病,一半是心病,心病还需心药治啊。”
琴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,能够听到两位老人的对话。

病友说:“老哥,还是你养个姑娘好啊,天天陪你打吊针,嘘寒问暖。”
父亲说:“都好,都好。你儿子也经常来看你哦。兄弟,你有什么心病,能告诉我吗?”
父亲这一问,病友便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题。
老哥啊,我有两个儿子,一个开货车跑运输,一个在家盘田种地,都已成家立业。两个儿子分家后,我则和老伴共同生活。
半年前,两个儿子商量,决定帮我们养老,按照农村的风俗,大儿子养爹,小儿子养娘。
听到儿子们的安排后,我第一是高兴,孩子们没有忘记养育之恩,能反哺父母了。第二是担忧,我们年事已高,不论做什么事也力不从心了,只会给孩子们增加负担。还有,我们两个老人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与年轻人会有冲突,能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吗?
一天晩上,我再次与老伴商量,看看该作何选择。
老伴默默地从床头柜抽屉里摸出来一本银行存折。唉,忙了一辈子,累了一辈子,熬了一辈子,苦了一辈子,存折里的金额实在羞于见人,远远不足以承载今后生老病死的支出。
夫妻俩四目相对,一脸的无奈和心酸。

老伴说:“不用商量了,随了孩子们的心愿吧,养儿不就是为了防老吗?”
我只有应和着说,好吧,听您的,谁让我们的“腰窝油”不肥厚(歇后语,云南人形容钱少)呢!
不日,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老夫妻,收拾起简单的行李,一步一回头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,相互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后,各自搬进了儿子们安排好的楼房里,开始了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。
我是做爹的,住大儿子家。住进儿子家才半个月,就感到浑身不舒坦。
儿子早出晚归跑运输,儿媳对我也很客气,客气到有点生疏冷漠。
儿媳喜欢打麻将,早饭后手机里不时传来"三缺一"的催促声。
每个白天,孙子去上学,我除了看看电视或到村口大榕树下找老伙伴拉拉家常外,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。
做晚饭的时间到了,儿媳迟迟未归。我呢,总不能袖手旁观地等人伺候吧,只好淘米择菜,洋相百出地学习做饭炒菜。
饭桌上,儿媳的脸上有时阴雨绵绵,有时嘴里嘟嘟哝哝,明显表示我做的饭菜不对味口,我心生愧疚,忐忑不安。

想多了心情就不爽,吃不下饭。
夜深人静的时候,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,我心里寡淡寡淡的,翻来覆去睡不着觉,十二分地想念我那在同一口锅里吃了几十年饭菜的老伴。
从前,与老伴虽然住在条件简陋的老宅里,但每天形影不离、相依相伴、彼此抚慰,有病互相精心地服伺,没病耐心地陪伴,吃着粗茶淡饭,也觉得很适合胃口,很满足。而现在,想想心里就堵得慌。
人老啰,不中用了!
唉,紧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叹息,
琴听见父亲安慰道:“兄弟,想开一点吧,我们这些人以前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罪还少吗?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就告诉自己的儿子,不能老憋在心里。
我有时也想,人老了,都会遇到很多问题,能及时解决当然是最好的了,接受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态度,最糟糕的就是既没有能力解决问题,又不愿意接受现状,每天抱怨,闷闷不乐,把自己的生活活成死局。有了这种心病,就像你自己所说的,那就真的无药可治了!”
病房内没有声音了,两位老人都陷入了沉默。
琴坐在病房外,两位老人的对话清晰地传进她的耳朵里,她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,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摄影 小夫(路开文化)
▼


沈丽华,云南玉溪人,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