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文/罗少华

童年时候的一大乐趣,就是难得一见的爆炒米。
爆炒米大爷,挑着一担挑子。挑子的一头的是标志性的、黑乎乎的、圆肚的“炸弹”;另一头是一个铁支架。他边走边喊:“爆—炒—米咯”,现在想来,那声音依旧萦绕耳边。
小时候家家都没有零食,能够吃饱一天三顿饭就不错了。爆炒米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额外加餐。
原料不要钱,从自家米缸里盛出一升米就好。燃料也不要钱,自家灶间装些木炭。大部分时间连加工费都不用出——这就要再多装些木炭,用这些多出来的木炭扺扣加工费。
唯一躲避不过去且必须花钱的环节,是给炒米加调味料,把米倒进“炸弹”肚子的时候,大爷会伸手问你要两分钱。收到钱后,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着的小纸袋,展开,将纸袋里的一小撮白色粉末,倒进炸弹肚子。白粉是用白砂糖压成的,有了它,爆出来的炒米才有甜美的味道。
炒米加不加料(白糖粉),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分水岭、试金石。
我是肯定拿不出来两分钱的,所以我家爆出来的炒米是“素”的。
爆炒米大爷有一个小帮手,是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子。大部分时间她闲着,显出她作用时是在爆炒米要起爆的时候。大爷用一根铁棍,将要撬动一个开关,此时的她,便要拿着一个大布袋紧紧兜住炸弹口,接住“嘭”的一声后崩出来的香喷喷的炒米。
闲着的时候她会轻轻的唱歌儿。

哎呀嘞哎!
打支山歌过横排.
横排路上石崖崖;
哎呀嘞,
哎呀走了几多石子路,
你格晓得啀细妹子,
着烂几多烂草鞋。
哎呀嘞哎!
我问她:“你参加了学校的文宣队吗?”
她略有些羞涩地看着我摇头,说她没有进过学堂。
我不信,想趁她还没反应过来,有意试她。我把手里的连环画递给她:“你没有进过学堂,小人书上面印的字你怎样认得呢?”
她好惊讶地拿过连环画去翻看,然后告诉我:上面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。
她喜欢看连环画,我就把我的收藏一本一本拿来给她。
她极聪明,只要听我把连环画上的故事说个梗概,她就能根据画面,一页一页发挥想象说出详细的情节来。有一本描述旧社会穷人受苦的连环画《一块银元》,她说着说着竟然被自己的述说感动,热泪盈眶,泣不成声。
她发现了我交不出给炒米加调味料的两分钱,在大爷向我伸手的时候,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袋,放在大爷摊开的大手掌上。大爷看看她,又看看我,笑笑。
她告诉我,她叫米桶。我问她是小名吗?她就好奇怪的看着我。

我最奇怪的是她的头发嫩黄嫩黄的,象冬天野地里枯萎了的草,让我想起“黄毛丫头”这个词语。我问她为什么头发是黄色的呢?她说不清楚,问我是不是吃油太少?
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她,我就会有些想她。有新的连环画了,我会刻意收起来,想着等她来的时候给她看。想她的时候,会想起她之前在看那些看过的连环画时,根据画面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故事情节,常常会被她逗得暗自发笑。
姐姐的辫子又粗又长,她剪下来要拿去卖钱,说卖了钱买个新书包给我。
我看姐姐把辫子放在枕头下,就把它偷偷拿走藏起来。
姐姐发现枕头下的辫子不翼而飞,急得茶不思饭不想,翻箱倒柜的找。
看着姐姐急,我不说话。
我想着等米桶下次来的时候,把姐姐的辫子送给她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,反正就是一个念想,我不想她一直都是个黄毛丫头。
摄影 小夫(路开文化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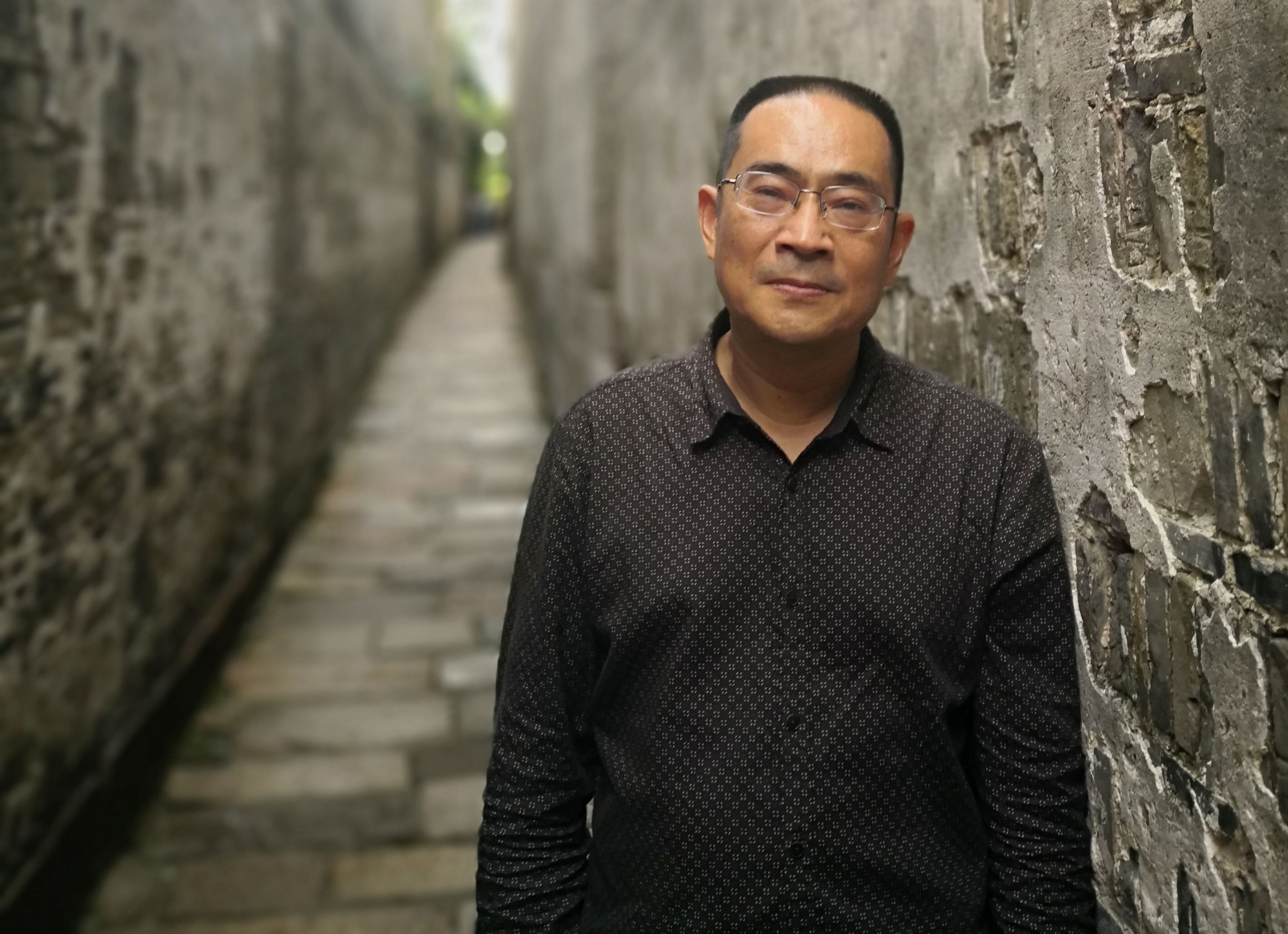
罗少华,赣州人,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人,现为广州某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。

童年时候的一大乐趣,就是难得一见的爆炒米。
爆炒米大爷,挑着一担挑子。挑子的一头的是标志性的、黑乎乎的、圆肚的“炸弹”;另一头是一个铁支架。他边走边喊:“爆—炒—米咯”,现在想来,那声音依旧萦绕耳边。
小时候家家都没有零食,能够吃饱一天三顿饭就不错了。爆炒米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额外加餐。
原料不要钱,从自家米缸里盛出一升米就好。燃料也不要钱,自家灶间装些木炭。大部分时间连加工费都不用出——这就要再多装些木炭,用这些多出来的木炭扺扣加工费。
唯一躲避不过去且必须花钱的环节,是给炒米加调味料,把米倒进“炸弹”肚子的时候,大爷会伸手问你要两分钱。收到钱后,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着的小纸袋,展开,将纸袋里的一小撮白色粉末,倒进炸弹肚子。白粉是用白砂糖压成的,有了它,爆出来的炒米才有甜美的味道。
炒米加不加料(白糖粉),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的分水岭、试金石。
我是肯定拿不出来两分钱的,所以我家爆出来的炒米是“素”的。
爆炒米大爷有一个小帮手,是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子。大部分时间她闲着,显出她作用时是在爆炒米要起爆的时候。大爷用一根铁棍,将要撬动一个开关,此时的她,便要拿着一个大布袋紧紧兜住炸弹口,接住“嘭”的一声后崩出来的香喷喷的炒米。
闲着的时候她会轻轻的唱歌儿。

哎呀嘞哎!
打支山歌过横排.
横排路上石崖崖;
哎呀嘞,
哎呀走了几多石子路,
你格晓得啀细妹子,
着烂几多烂草鞋。
哎呀嘞哎!
我问她:“你参加了学校的文宣队吗?”
她略有些羞涩地看着我摇头,说她没有进过学堂。
我不信,想趁她还没反应过来,有意试她。我把手里的连环画递给她:“你没有进过学堂,小人书上面印的字你怎样认得呢?”
她好惊讶地拿过连环画去翻看,然后告诉我:上面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。
她喜欢看连环画,我就把我的收藏一本一本拿来给她。
她极聪明,只要听我把连环画上的故事说个梗概,她就能根据画面,一页一页发挥想象说出详细的情节来。有一本描述旧社会穷人受苦的连环画《一块银元》,她说着说着竟然被自己的述说感动,热泪盈眶,泣不成声。
她发现了我交不出给炒米加调味料的两分钱,在大爷向我伸手的时候,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袋,放在大爷摊开的大手掌上。大爷看看她,又看看我,笑笑。
她告诉我,她叫米桶。我问她是小名吗?她就好奇怪的看着我。

我最奇怪的是她的头发嫩黄嫩黄的,象冬天野地里枯萎了的草,让我想起“黄毛丫头”这个词语。我问她为什么头发是黄色的呢?她说不清楚,问我是不是吃油太少?
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她,我就会有些想她。有新的连环画了,我会刻意收起来,想着等她来的时候给她看。想她的时候,会想起她之前在看那些看过的连环画时,根据画面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故事情节,常常会被她逗得暗自发笑。
姐姐的辫子又粗又长,她剪下来要拿去卖钱,说卖了钱买个新书包给我。
我看姐姐把辫子放在枕头下,就把它偷偷拿走藏起来。
姐姐发现枕头下的辫子不翼而飞,急得茶不思饭不想,翻箱倒柜的找。
看着姐姐急,我不说话。
我想着等米桶下次来的时候,把姐姐的辫子送给她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,反正就是一个念想,我不想她一直都是个黄毛丫头。
摄影 小夫(路开文化)
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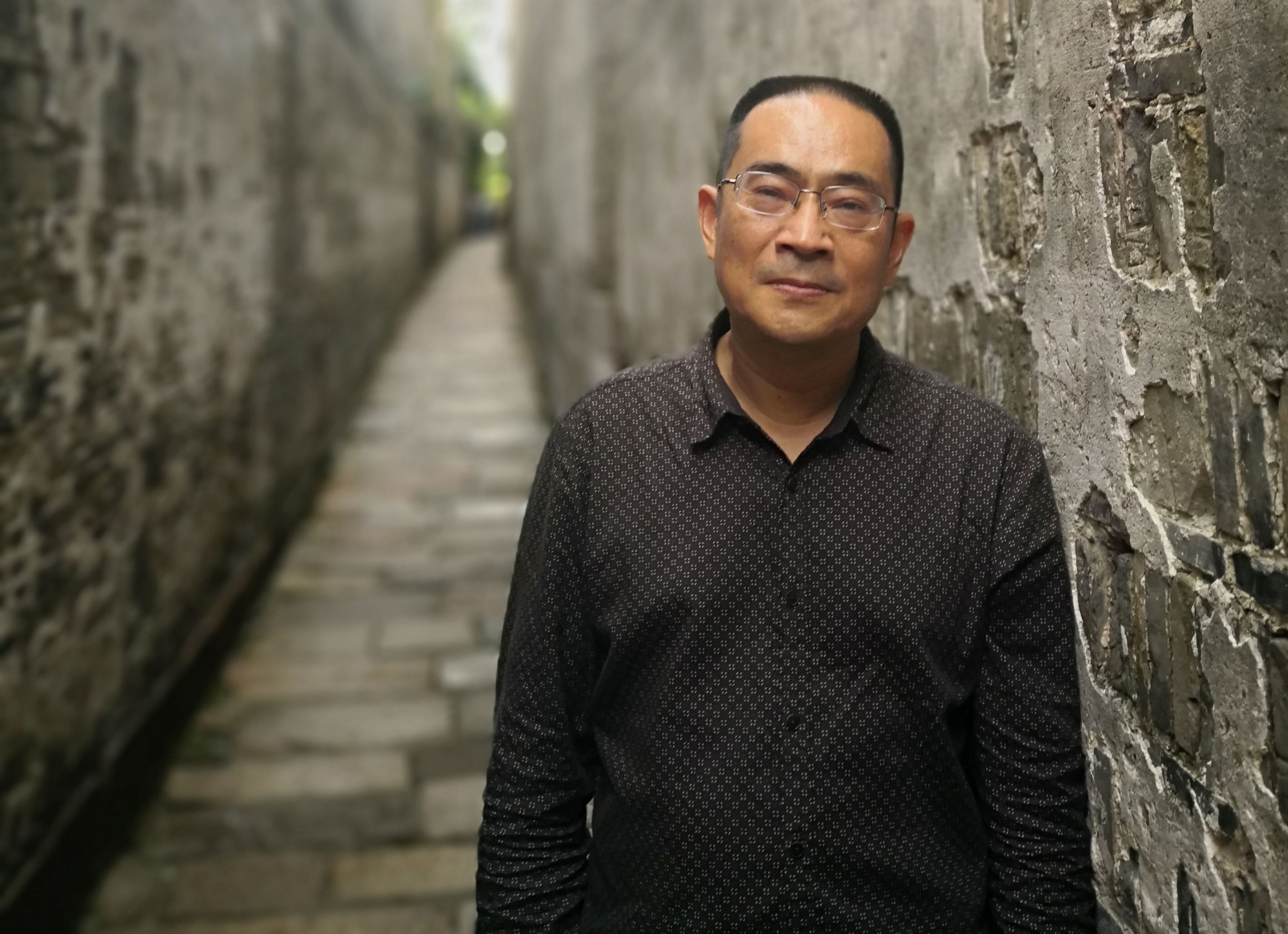
罗少华,赣州人,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人,现为广州某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。

